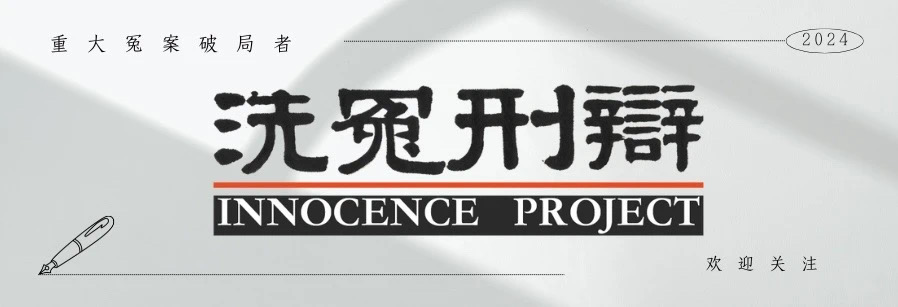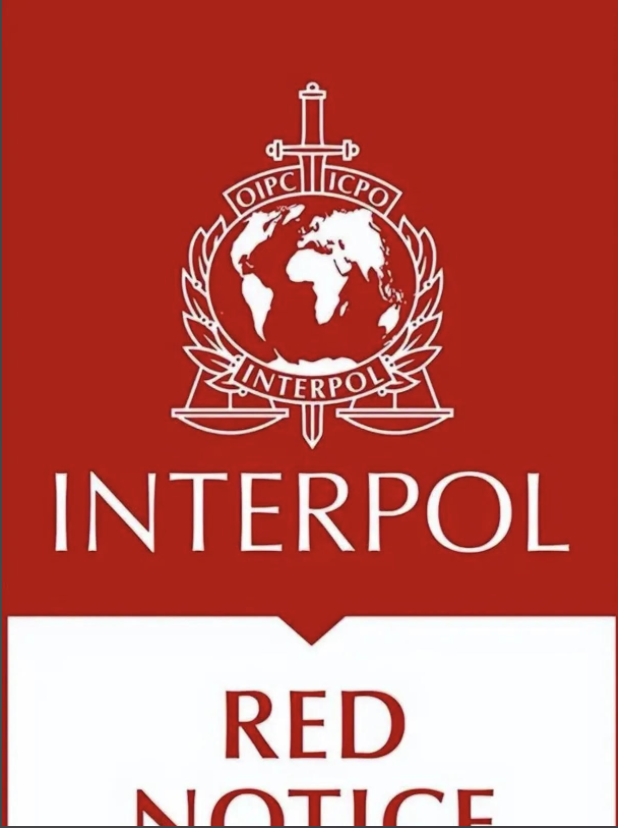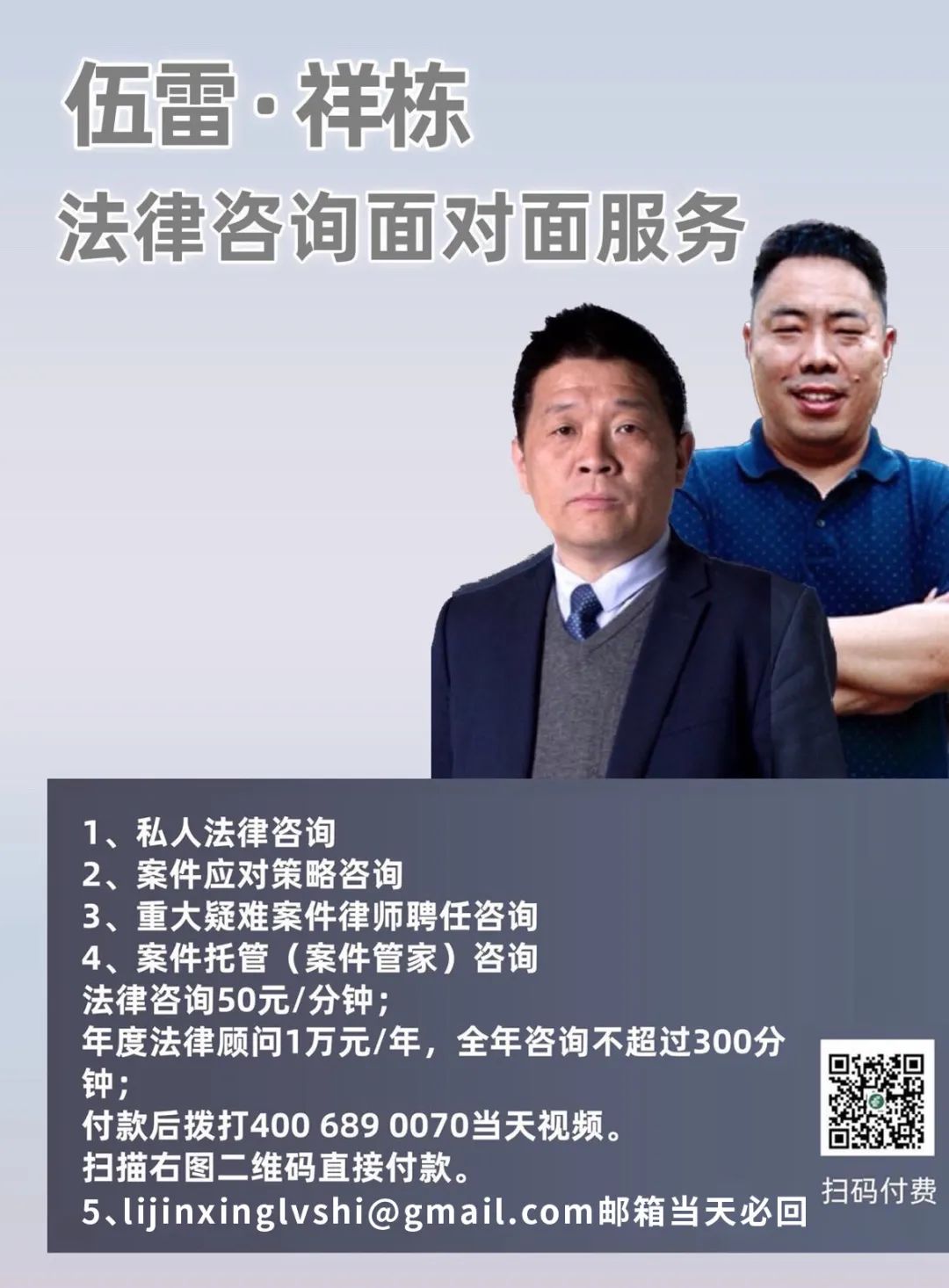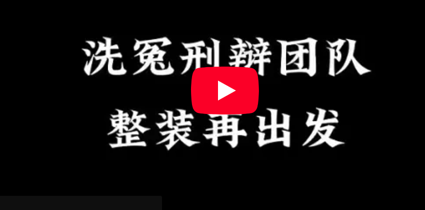洗冤刑辩|2024年最后2天,全案去除“恶势力”
12.30
全案去恶
近日,青石刑辩团队的金磊、冷慧、陈立强和张涛四位律师在中部某省办结一起未成年人被控涉恶案件,一审法院判决全案不构成恶势力,量刑大幅度降低,判决已于12月30日生效。
案件背景:7人涉恶,违法管辖
起诉书指控8名被告人中的7名构成恶势力,7名被告人中又有5名未成年人。指控的绝大部分事实的发生地和结果地均在该省B市,在没有任何合法规范的指定管辖文书时,A市公安机关便前往B市抓捕多名被告人,这导致立案之前就存在案件管辖权的争议。
审查起诉阶段,青石刑辩团队接受委托,金磊律师第一时间介入案件,约见检察官,详细阐述了案件不构成涉恶的法律意见,并提出案件事实证据和侦查取证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检察院在临近春节、第一次补充侦查结束后的第13天,仍将涉案当事人以涉嫌恶势力犯罪起诉至法院。
审理阶段,冷慧律师、陈立强律师、张涛律师先后加入辩护团队,法院共计安排了两次庭前会议和三次正式庭审,充分听取检察院和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表现出了对案件的高度重视,努力实现裁判的程序和结果公正。
办案经过:人为拔高定性,阅卷困难,辩护人积极争取

(辩护律师:冷慧律师、金磊律师、陈立强律师、张涛律师)
事实上,律师的辩护工作并不容易。
- 首先,律师自始至终坚持认为此案不构成恶势力,定恶存在拔高凑数的嫌疑。起诉书列举的涉恶行为、人数、时间等事实要素前后矛盾,涉恶人员混乱又模糊不清,无法确定出一个符合法律规定的“恶势力团伙/组织”,起诉书还有关键人员信息不明、指控事实不清的问题。辩护人先后多次建议检察院变更起诉书内容。该问题的纠正过程相当曲折,难以言表,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反映,公诉机关终于在第二次开庭时才决定制作书面变更起诉书移送至法院,但涉恶指控仍然存在。
- 其次,律师阅卷权的行使需要极力争取。此案存在大量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证据,还有数十张光盘的讯问同录。起初,律师无法复制上述证据,经过多次说理、沟通和申请,法院最终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律师的阅卷权。开庭时,通过播放案发现场的视听资料,经由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合议庭依法认定了案件事实。
- 最后,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规定对辩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案有作为当事人的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司法机关的行为需要符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中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制度要求,同样的,隐私保护、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等规定,也要求律师更要依法依规辩护。
努力终见成效,多方因素共同作用,摘除“涉恶”帽子
尽管经历了一次变更起诉,但去除涉恶指控的辩护工作仍需继续。
开庭期间,通过紧密的法庭调查,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均认为不构成恶势力。结合控方的举证质证和公诉意见,辩护律师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要件和案件实际出发,对所有被告人被指控涉恶的事实进行了分析论证、概述说明,充分发表了全案不构成恶势力的意见。
休庭以后,律师又形成了多份书面法律意见,在与合议庭保持沟通的基础上,表达希望法院能正确适用法律。
三个月后,法院作出了不构成恶势力的判决,拿掉恶势力的帽子。多名被告获从轻量刑,相较于检察院建议,减轻三年以上。
宣判以后,无一名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未抗诉,判决现已生效。
在刑事辩护环境如此复杂的当下,涉恶案件的启动可能非常简单,但通过辩护纠正错误指控却非常艰难。办理该案的金磊、冷慧、陈立强和张涛,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刑辩律师,既具备丰富专业的法律知识,又不失应有的勇气和决心。办案期间四位律师召开6次以上的案件研讨会,各自均会见当事人5次以上;与检察院、合议庭多轮沟通解决分歧,又向不同政法单位反映案件办理中发现的问题。律师的步步为营,全面制定辩护方案,最终最大化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然,正如伍雷所言,一个案件的成功永远离不开当事人的坚定和家属的信任。此案家属在寻找律师的过程中也走过弯路,但与四位律师建立委托以后,便积极配合律师提出的辩护方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对律师展现出了百分百的信任,案件取得好的结果与他们的坚定选择和完全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同时,被告人、家属和律师也很感谢法院合议庭、审委会有所担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认定被告人不具有恶势力形成时间、人数和“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所具备的行为动机、行为表征、非法后果等构成要件要求,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判决宣告恶势力不成立,保护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判决不构成恶势力,意义重大
在当下涉恶案件的认定泛滥化、办案流程形式化和辩护空间如此逼仄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坚持、家属信任和律师的全力辩护,说服法院采纳不构成恶势力的观点,将偏离方向的刑事案件拉回正轨;法院通过判决方式去恶,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和担当。
一份经得起检验的判决,既是对侦查和审查起诉中不合法、不合规行为的监督和纠正,也彰显了法律权威。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和家属、公众的正面评价,说明判决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治理上,该判决也有重要意义。
现行规范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有包括宪法、刑诉法、刑法、义务教育法等一般法律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特别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仅设置了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第九检察厅,还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强调加强制度建设。
然而,实务中未成年人不断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被害人(特别是共同犯罪中),大量司法行为也未能重视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部分制度未能落到实处,无法通过个案形成长效保护机制。
青石刑辩团队在办理多起涉未成年人案件时发现,大量当事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原生家庭并不和谐,他(她)们在各种无意识、无能力的时间段实施了犯罪行为或遭受了不法侵害;部分当事人还存在精神或心理疾病。司法机关在社会调查时,调查形式单一,更多地依赖纸面材料,缺乏实地走访、心理测评等调查环节,形成的调查意见片面。加上后期追踪保护的机制不完善,导致帮扶教育和刑法预防的效果大大减弱。
又有,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均有多项工作指引和制度规定,如询问未成年人被害人时,就有“一次询问”、“一次不超过一小时”、“应当同步录音录像”等规定要求。然而,办案机关在取证时普遍存在不符法定规范的行为,多次询问、单独询问、异性主体询问、不进行录音录像的现象时常发生。审判机关通过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监督,排除非法证据,对案件的错误定性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倒逼侦查机关合法取证,将各项保护未成年人制度规定落到实处。这也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种思路。